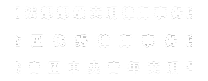新闻中心
专业为本 追求卓越
|
微信红包赌博行为定性问题探讨时间:2020-07-13 引言
案例二:2016年7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甲伙同被告人陈某乙、同案人员季某经事先商议,由被告人陈某甲在微信上建立微信群并设定抢红包规则用于赌博。陈某甲以“免死”的身份(抢到红包金额即为渔利,即使抢到特殊号码也无需按规则发一个与特定数额相等的红包)抢红包;被告人陈某乙及同案人员季某分别负责赌场的奖金发放和赔付,并从被告人陈某甲处拿取每人每天200元的酬劳。 案例一中,法院判处被告人桑某、刘某的行为构成赌博罪;案例二中,法院判处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等构成开设赌场罪。 司法实践中对以上述模式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红包赌博的行为在定性上并不一致,目前主流观点一般将其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但司法界也存在不同声音,即认为构成聚众赌博罪。
第一,微信红包赌博符合赌博罪中聚众赌博的构成要件。微信群不具有开放性,进入微信红包赌博群需要经过群主或者管理员的审核通过,它不能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完全开放,具有相对封闭性。同时,群主或管理者对于微信群掌控的程度也远不如现实中对开设赌场的场合的掌控程度。因此,微信红包赌博群与传统意义上的赌场具有一定的区别,也不能解释为赌博网站,它不符合开设赌场罪的客观方面。 第二,将其认定为赌博罪更符合刑法的谦益性。开设赌场罪和赌博罪都规定在刑法的第三百零三条,二者在犯罪构成和罪行标准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由于开设赌场与一般的赌博犯罪相比,具有更高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罪单独设罪,并将其最高刑期提高到了有期徒刑10年,使得其处罚要求高于一般的赌博罪。所以,在将某种行为认定为赌博罪还是开设赌场罪难以确定时,应将该种行为认定为较轻的赌博罪。 第三,将微信红包赌博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不符合《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由于在《意见》中对于开设赌场行为的情形采用的是有限列举的方式,因此,在认定开设赌场罪时,不仅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利用网络、移动终端的情形,还要判断是否符合四个具体情形中的一种。在微信红包赌博中,虽然行为人利用了网络及手机进行犯罪活动,但是并不符合《意见》所规定的四种具体情形。 认为应将微信红包赌博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人持有以下观点: 第一,微信红包赌博群可以被认定为赌场。微信红包赌博群与传统意义上的赌场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只是在形式不一样,将其认定为赌场属于扩大解释,并没有超出社会公众的预期。而且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第二条,还是《意见》的第一条,都为将网络和移动设备定义为开设赌场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微信红包赌博群的群主或管理者对赌场及赌博活动具有绝对支配力。组织者对于赌场及赌博活动的支配力是区分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聚众赌博中,参赌人员一般是在小范围的圈子里,组织临时性的赌博活动,参赌成员相对稳定。但是,对于赌博的场所却没有要求,因此,组织者对于赌场的支配力较小。而在微信红包赌博群里,群主或管理者可以自行制定赌博活动的规则、决定群成员的去留及微信群的存灭,对于赌博群来说是具有绝对支配力的。 第三,将微信红包赌博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开设赌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赌博参与者的赌博行为。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行为人通过微信平台建立微信群,并制定群内的相关赌博规则,引诱他人加入,在该微信群的赌博活动中,起绝对作用,其主观恶性较大,行为模式也与开设赌场行为一致,应当按照处罚要求更高的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第四,将微信红包赌博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与《解释》的规定是相一致的。2010 年的《解释》中就规定了利用网络平台或相关的通讯终端设备进行传输数据赌博,或者建立相关网站赌博的,或者参加赌博网站中的利益分成的其中之一行为就是开设赌场。微信红包赌博就是利用微信这一社交软件,通过建立即时聊天的微信群,并利用该社交软件传输金钱,通过下注抢红包来实现赌博的目的。微信群主与代包手在赌博过程中抽头营利,这与《解释》中的规定相一致。
微信红包赌博犯罪与开设赌场罪、赌博罪在本质上是相同,但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其在形式上还是有自己的特殊性。准确定性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行为,关键要厘清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的本质区别。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第十八条将开设赌场罪从赌博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定罪名,两罪的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有观点认为,“赌场”的存在是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核心区别之一,与聚众赌博的场所相比,开设赌场罪名中的“赌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如人员、场所较固定,并且更具有持续性。但事实上聚众赌博中也需要赌博场所,参赌人员也可能在固定的场所、时间聚众赌博。 目前关于“赌场”的界定并无规范的认定标准,所以,以“赌场”为标准判断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难以从根本上对两罪进行区分。可以认为,“赌场”或“赌博场所”,是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中共同具备的要素,不同之处在于开设赌场客观方面侧重于“开设”,开办、设立,即行为人对赌场的“控制性、经营性”,而聚众赌博对此并无要求。 具体认定开设赌场行为时,如何判断行为人对赌场或赌博场所的“控制性”、“经营性”这一特征呢? 笔者认为,“控制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人能够掌控赌场的经营时间、赌博方式、抽头比例,对赌博场所、赌场内部组织和经营等整个赌博活动享有支配地位。开设赌场是以赌场为依托从事营业性活动,必然要求行为人采取一定的经营管理行为以维持赌场的正常运转,也就是所提到的“经营性”。行为人所控制的赌场内部分工明确,会提供各种经营服务,以维持赌场的运营。而聚众赌博只是组织、召集、聚拢参赌人员进行赌博,并不具有经营赌场的行为特性,对赌场的控制力也相对较弱。
要对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行为作出准确定性,需结合前文中对于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的分析界定把握。 根据前文分析,在微信抢红包赌博案件中,以赌场为中心的判断标准无法解决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定性问题。此时,应更多考察行为人对微信群的“控制性”和“经营性”。其中,行为人的“控制性”主要体现在制订相关的赌博规则,并按照规则运营微信群,如一旦发现群成员不遵守制定的规则,则会给予违反规则者移除出微信群的惩罚。行为人需要对群内的赌博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使赌博活动能够长期稳定的持续下去。“经营性”主要体现在赌博微信群内行为人的明确分工。一般来讲,为保障赌博活动的持续性,发起人会召集他人进行分工合作,如雇佣发包手、统计人员等。 在上文案例二“陈某甲、陈某乙等开设赌场案”中,陈某甲为参赌人员提供赌博的场所,同时组织召集其他行为人一起分工合作,担任发包手、财务等具体维护赌场运营的工作。通过设置的赌博方式、赌博规则,组织召集参赌人员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综合来看,陈某甲行为的本质是设立微信群并对在该微信群中进行的赌博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并从中获取收益,应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如果行为人建立微信群,只是聚集人员抢红包赌博的,并未对微信群进行实质经营管理,则该行为宜认定为聚众赌博。 在微信红包赌博案件中,厘清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的界限标准,重点考察行为人在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赌博的过程中是否具有“控制性”、“经营性”,从而作出准确定性。对于行为人出于娱乐目的而在相熟的亲戚朋友间抢红包的,不以赌博罪论处;召集人员在开放式微信群进行抢红包赌博,没有人员分工等经营行为的,应认定为聚众赌博;组建微信群进行抢红包赌博,对赌博活动具有支配性、经营性的,应认定为开设赌场,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 陈颢珺. 赌博行为犯罪化与非罪化的思考[D].中国人民大学,2008. [2] 陈柳清.“微信红包”赌博活动的犯罪学探究[J].北方经贸,2017(07). [3] 董天园.微信红包群涉赌案件的实证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7(04). [4] 杜斌,阮方民,李永红,乐绍光,梁敏捷,杨赞,王盛,赵洁瑶.利用微信“抢红包”聚赌行为如何处理[J].人民检察,2016(10). [5] 范蕾蕾. 微信红包赌博犯罪问题研究[D].贵州民族大学,2017. [6] 李连华,鞠佳佳.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的界限[J].中国检察官,2009(04). [7] 林丹丹.从组织架构谈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区别[J].中国检察官,2017(16). [8] 罗开卷,赵拥军.组织他人抢发微信红包并抽头营利的应以开设赌场罪论处[J].中国检察官,2016(18). [9] 邱利军,廖慧兰.开设赌场犯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六)》和“两高”关于赌博罪司法解释为视角[J].人民检察,2007(06). [10] 邵海凤.《刑法》第303条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以“两高一部”关于网络赌博犯罪司法解释为视角[J].法治论丛,2011(1). [11] 宋君华,邢宏伟,陈启辉.开设赌场罪与聚众赌博罪之区分应重点判断行为人对赌博活动的控制性[J].中国检察官,2012(24). [12] 杨晶晶. 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若干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6. [13] 于志刚.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规律分析与制裁思路——基于100个随机案例的分析和思索[J].法学,2015(03). [14] 张建,俞小海.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红包的行为应定为赌博罪[J].中国检察官,2016(18). [15] 周立波.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红包赌博的定性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03). [16] 宗凤月.新型社交网络赌博犯罪的进化——以‘微信红包’变相赌博为例[J].犯罪研究,2016(05). 作者简介
高雅律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业务领域:刑事辩护、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及物业法律服务 组稿、统筹/石文娟 编辑、排版/张梦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