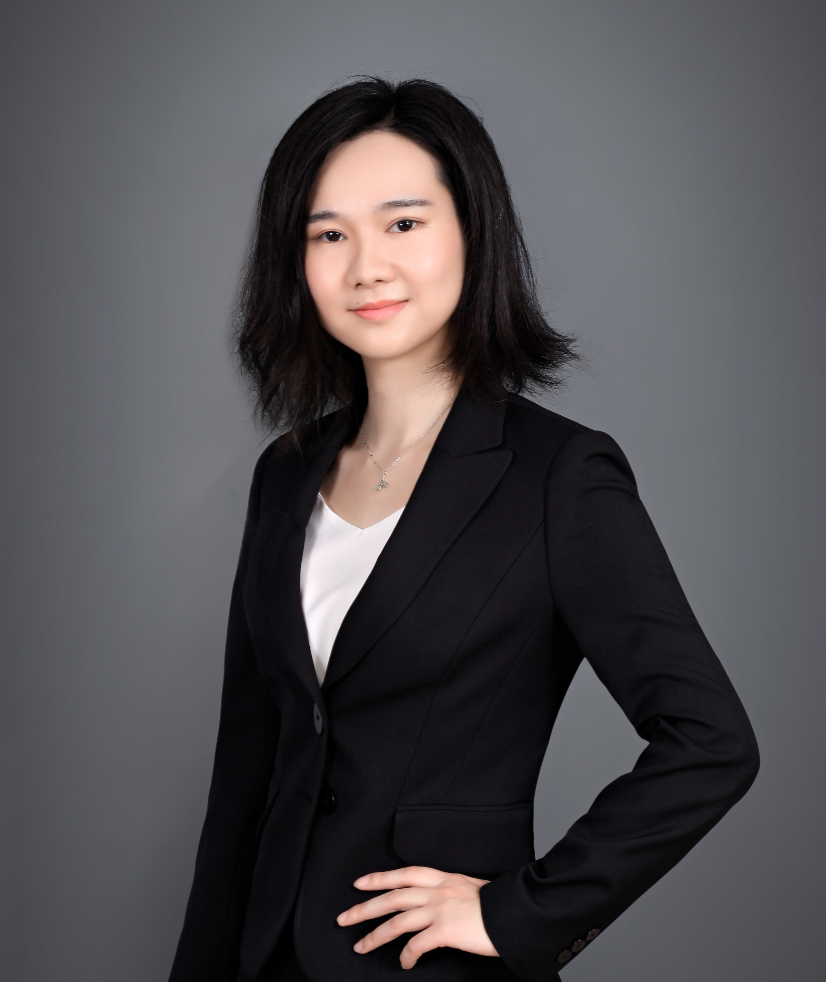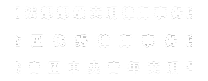新闻中心
专业为本 追求卓越
|
最高额抵押担保中的最高债权额问题时间:2020-07-13 商业实践中,由于现行法律对最高额抵押担保中的最高债权额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且理论和司法裁判对于该等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导致裁判结果不统一,交易双方难以形成合理预期,妨碍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和交易效率的提高。最高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一定程度上为弥合分歧、提升最高额抵押制度的确定性提供了问题解决思路。 一、有关最高限额认定的理论及实践 对于最高额抵押权的最高限额的范围界定,理论上存在“债权最高限额说”和“本金最高限额说”两种观点。[i]债权最高限额说认为,原债权、利息、迟延利息及违约金合并计算所得受偿的债权最高限额,其共超过部分,无优先受偿权。本金最高限额说认为,以“原债权”作为得受偿的最高限额,原债权以外之利息、迟延利息及约定担保之违约金,仍为担保权效力所及,不受该最高限额的限制,共超过部分,仍得优先受偿。[ii] 据调研,在商业实践中,各银行使用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制式文本也分为两种类型。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采用债权最高限额说的理解,合同典型表述为“担保的债权/主债权的最高余额/最高限额”;中国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等则采用本金最高限额说的理解,合同典型表述为“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iii] 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处理结果大体可分为三种[iv]: 1.法院按照合同的约定予以认定,即合同约定最高债权限额的,适用债权最高限额说裁判;合同约定最高本金限额的,适用本金最高限额说裁判。 2.法院作出与合同的约定相反的认定,即合同约定最高债权限额的,适用本金最高限额说裁判;合同约定最高本金限额的,适用债权最高限额说裁判。 3.当事人没有约定最高限额的标准时,法院直接适用债权最高限额说或者本金最高限额说裁判。 二、现阶段司法裁判倾向分析 现行《担保法》和《物权法》均未明确“最高债权额”是否包含本金之外的利息等其他费用,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亦未对相关规定予以实质性修改或者补充。 (一)关于九民纪要[v]第58条的解读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称“最高院”)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第58条规定:“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一般应当以登记的范围为准。但是,我国目前不动产担保物权登记,不同地区的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并不一致,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充分注意制度设计上的差别,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一是多数省区市的登记系统未设置‘担保范围’栏目,仅有‘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的表述,且只能填写固定数字。而当事人在合同中又往往约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致使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与登记不一致。显然,这种不一致是由于该地区登记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造成的该地区的普遍现象。人民法院以合同约定认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是符合实际的妥当选择。二是一些省区市不动产登记系统设置与登记规则比较规范,担保物权登记范围与合同约定一致在该地区是常态或者普遍现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以登记的担保范围为准。” 根据最高院民二庭关于该条的释义,该条规定解决的是关于合同约定的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时,应以何者为准的问题。[vi]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表明,九民纪要倾向支持以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进行裁判,同时,在国家大力倡导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九民纪要的精神也体现了“本金最高额”的观点。[vii] 应当说,九民纪要第58条并没有实质性解决关于最高债权额的登记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问题,但作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完善过程中的过渡性方案,最高院这一贴合实际的务实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该条表明最高院在相对人合理信赖保护和公平对待债权人两相权衡下,选择优先保护交易公平。但要判断该条是否隐含了最高院对最高债权额理解的某种倾向,或许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支持。 (二)关于最高院新近判例的解读 虽然,九民纪要第58条未对最高限额认定应当采“债权最高限额说”还是“本金最高限额说”进行明确表态,但是,最高院现阶段在该问题上的裁判倾向,或可从其在九民纪要发布前后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823号”判决书[viii]中窥见一斑。 最高院在该份二审判决书中写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各担保人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5亿元整’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即各保证人所担保债权最高额限度为本金5亿元和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律师费、保全费实现债权费用等均属于被担保债权范围。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亦应依约履行。……本案已查明,至本案一审庭审时本案未偿还借款本金为492443528.38元,该数额并未超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本金5亿元,故各保证人应以合同约定对华美奥公司的涉案债务本金人民币5亿元和实现债权的律师费、保全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各保证人仅在5亿元最高债权额限度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可以看出,最高院在该案中是明确支持“本金最高限额说”的。其在二审判决中径行改变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最高额担保合同仅约定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而未约定最高债权限额的“非典型最高额担保”有效,该等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除债权本金之外,实际发生的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与债权本金之和超过约定最高限额的部分,亦属于被担保债权的范围。 三、采用本金最高限额说的合理性分析 对最高限额的不同理解,将影响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的优先受偿范围,并且,在存在多重抵押的场合,对于后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抵押人的其他债权人对抵押物余值的期待利益等均产生影响。因此,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债权最高限额说”和“本金最高限额说”之间作出最终选择。 概言之,支持债权最高限额说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本金最高限额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文义解释,合同约定本金最高额有违物权法定原则。第二,本金最高限额说有违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在先被担保债权总额不确定,有损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合理信赖利益。第三,本金最高限额说导致担保债权突破最高限额,实质上变成无限额担保,破坏了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第四,参照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成熟做法,如日本、德国以及台湾地区债权最高限额说为主流学说,立法也均采纳该观点。[ix] 笔者认为,债权最高限额说确有其自洽的法律逻辑和法益保护倾向。但是,相较而言,债权最高限额说远不及本金最高限额说贴合商业逻辑、符合商业实践和满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而最高院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裁判倾向上再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一)最高限额范围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 《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关于物权的创设,我国采法定主义,即法律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不允许当事人依其意思设定与法律规定不同的物权。[x]但是,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我国现行法律,对最高额担保中的最高限额的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认为仅约定债权本金最高限额是对最高额担保法定内容的超越,缺少法律依据。 基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应当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通过合同条款进行约定。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和立法解释的情况下,所谓的文义解释以及有关立法目的的推断都只能是臆测。 (二)本金最高限额说无损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和后顺位抵押人的信赖利益保护 诚如最高院在九民纪要第58条释义中所说:“基于现实的考量,本纪要采取了以合同约为准的处理方法。当然该规则一旦确立,对所有债权人都是公平的,后顺位债权人在设立抵押权时,就不能仅仅去看登记簿,可能还要看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另一方面,后顺位受益权人在登记簿上记载的尽管也是主债权,但其范围同样及于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相比更后顺位的抵押权人而言,对其的保护也是周全的。”[xi] 其实,实践中存在的有关最高限额范围的纷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我国现行物权登记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最高限额范围作为最高额抵押权的重要内容之一,理应纳入登记簿的记载范围,并与合同的约定保持一致。后顺位抵押权人基于该等登记簿记载信息产生的合理信赖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由于登记簿设置不当,而导致在先担保物权内容无法获得充分公示,其责任不在在先抵押权人,亦与是否采本金最高限额说无关。若因此归咎于在先抵押权人,限制其获取合法权益,对其实为不公。此外,在物权登记规范统一、登记内容详实、公示充分、查询自由的前提下,由于对最高限额范围的认定标准是统一的,采用本金最高限额说,并不会导致对在先抵押权人和后顺位抵押权人保护的不平等。 诚然,要求后顺位抵押权人了解合同有关最高限额范围的约定,可能会加重其注意义务。但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电子登记簿的使用已得到普及,登记查询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日益降低。因此,合理增加后顺位抵押权人的注意义务,并不会对交易效率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最高额抵押制度与普通抵押制度的衔接 最高额抵押制度相比于一般抵押制度的最大优势,即在于其圈定被担保债权范围机制上体现出的灵活性。最高额抵押与普通抵押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抵押权设立时被担保债权是否特定,而不在于当事人是否约定了“最高限额”。事实上,发生债权确定情形后,最高额抵押随即转为普通抵押,二者再无分别。如对普通抵押的附随债务的自然发生以及相应的担保效力不做限制,而在最高额抵押转为一般抵押之后,反倒因所谓的“最高限额”限制债权人对自然发生的附随债务的优先受偿权,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上经不起推敲。 如同只约定本金最高限额的最高额抵押一样,在普通抵押项下,抵押权设立时亦只能确定和登记债权本金的具体数额,其他诸如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附随债权的总额,仍须待抵押权实现时方能知晓;在不超过抵押物价值的前提下,抵押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按照主债权和附随债权实际发生总额计算。但是,我国法律并未因此禁止一个物上设有多个普通抵押权,也从不认为在先的普通抵押权担保的债权总额不确定有损后顺位抵押权人的信赖利益。因此,只因当事人额外约定了“最高限额”,而对最高额抵押区别对待,于法无据。 实际上,由于对最高限额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司法裁判混乱,使得市场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为确保其债权获得更为充分的保障以及规避抵押权实现时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已经出现了弃用最高额抵押而回归普通抵押的趋势。可以想见,如果执意继续适用债权最高限额说,将迫使债权人选择交易成本更高、交易效率更低的普通抵押,而最终背离最高额抵押制度设立的初衷。 (四)本金最高限额说是商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最高额抵押制度因其从属性的缓和而被广泛采用,被称为“今日金融市场之宠儿”[xii]。最高额抵押制度在商业实践中的迅速推广和广泛使用,与其制度上的便利性密不可分;反过来说,如果某项制度设计违背市场规律,无益于交易便利,或者过分倾向于保护某一交易方的利益,则该制度终将为市场所摒弃。 或许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发明者在最初设计这项制度时,确实因循过债权最高限额说的思路。但随着商业实践和附随、衍生债权计算规则的日益复杂化,人们发现,由于最高额抵押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将来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被担保的附随债权的具体数额进行交易规划、安排时根本不可能精确地加以估算。强行要求抵押权人为尚未发生的全部债权设定一个“最高限额”,实是强人所难。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本金最高限额模式对于债权最高限额模式的改良。 实践中,为了应对法院适用债权最高限额说,而可能导致的主债权无法获得全部优先受偿的风险,部分金融机构采取在债权本金数额的基础上拉高担保最高限额或者降低实际发放的贷款本金数额的做法,同时,额外要求第三人提供保证担保或要求债务人提供其他担保,以覆盖因附随债务的发生而可能形成的“担保真空”。这其实可以看做是司法活动对商业活动内在逻辑缺乏必要尊重而带来的社会总体交易成本的增加。 可见,采用债权最高限额说会使得债权人的交易风险上升,而债权人为转嫁该等风险将迫使债务人或第三人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担保,最终导致债务人融资成本上升,变相降低了债务人的融资能力,而这与我国当前着力于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经济政策格格不入。 结语 最高额抵押担保中最高限额的认定问题,最终仍需依托登记簿与合同约定的高度一致来获得根本性解决。在此,我们期待未来立法和司法能就该等问题给予明确回应,并做出能够契合商业需求和时代发展的最佳选择。 [i]本文所称“债权最高额说”和“本金最高额说”,与“债权最高限额说”和“本金最高限额说”具有相同的涵义。 [ii]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第376页。 [iii]参见吴楠、熊玮:最高额抵押“债权最高额说”与“本金最高额说”——兼析“最高额”的约定与判例。 [iv]此处参考了注释iii及魏星、丁晓雨所著《最高额抵押担保中“最高额”的司法认定——基于136份案例的实证分析》(该文发表于《天津法学》2018年03期)中所载数据。 [v]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称“九民纪要”、“纪要”,均系指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vi]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第357页。 [vii]参见姚惠惠:《九民纪要》之后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法律分析[OL] 。 [viii]参见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823号。 [ix]柯澄川,最高额抵押债权优先受偿的范围[J],人民司法,2019, (29):101-105。 [x]魏振瀛,民法(第五版)[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18页。 [xi]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第358页。 [xii]谢在全,银行联贷与最高限额抵押权[J]。法律适用,2018,13: 32-44。 作者简介
胡琛律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硕士 湖北省律师协会第八届金融、证券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检察院咨询专家组成员 业务领域:银行金融、商事投融资、基金、信托、债券、公司合规、商事争议解决等 组稿、统筹/石文娟 编辑、排版/张梦佳 |